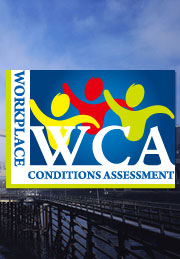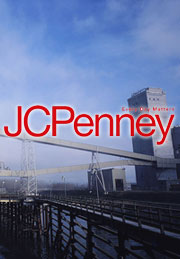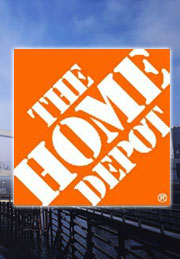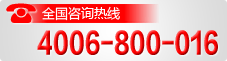電話:18605772928
地址:溫州平陽縣鰲江鎮(zhèn)金鰲路21幢
3單元201室
電話:021-51029391
手機: 18601606208
熱線:4006-800-016
郵箱:chaowang@tranwin.org
地址:昆山市花橋國際商務區(qū)兆豐路18號亞太廣場1號樓9樓(郵寄)
企業(yè)社會責任運動發(fā)展迅速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勞動者為維護其權益所開展的工人運動在經過18世紀的高潮后,于20世紀取得了明顯成就并繼續(xù)向縱深方向推進。析言之,無論是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還是在壟斷資本主義時期,勞動者為反抗資本家的剝削、改善自己的勞動條件和勞動待遇進行了長期不懈的斗爭。最初,勞動者反抗資本家的斗爭具有明顯的分散性和自發(fā)性特點,面對資本家的壓榨,他們通常采取破壞機器設備等簡單的方式發(fā)泄其不滿。隨著勞動者維權意識的逐步提高以及因企業(yè)規(guī)模的擴大而引起的勞動者愈加集中,勞動者反抗資本家的斗爭也更具組織性。他們紛紛建立和加入工會,舉行聲勢浩大的罷工或示威游行,以此對抗資本家,保護自己的正當權益。迫于勞動者的強大壓力,資本家不得不作出一定的讓步,勞資沖突在進入20世紀后也相應有了很大程度的緩和。然而盡管如此,勞動者的維權活動從未停息過。尤其是壟斷資產階級在其統(tǒng)治地位鞏固后不久普遍對工會和工人運動采取敵視態(tài)度與高壓政策,激起了工人階級的極大憤慨;30年代的“大蕭條”以及以后的“滯脹”,又使通貨膨脹、失業(yè)、工資等問題及其導致的勞資矛盾更加尖銳,并由此引發(fā)了勞工與企業(yè)界之間一次又一次的大規(guī)模沖突。在勞資爭議中,勞動者的著眼點由一度放在眼前和局部經濟利益上逐漸轉向重視長遠與整體利益的保障上,工資、工時、就業(yè)保障、組織工會的權利、社會保險及福利待遇、職業(yè)安全與保健、集體談判、職工參與等都成為近幾十年來工人運動關注的重要事項。在政府的協(xié)調下,資本主義國家在當今都從總體上最終實現(xiàn)了由工業(yè)專制向工業(yè)民主的過渡,大企業(yè)也一改單純的高壓政策而采取“胡蘿卜加大棒”式的策略調整勞資關系,從而使勞動者的境況有了很大改善,這些都與20世紀勞動者有組織的維權運動是分不開的。
其次,自然資源和環(huán)境保護運動在20世紀邁上了一個新的臺階。早在19世紀,資本家對自然資源肆無忌憚的掠奪以及由此造成的嚴重后果,即引起了一些科學家和開明人士的高度重視,他們向當局提出建議,要求國家切實保護自然資源和生態(tài)環(huán)境,在民眾的推動下,各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也先后出臺了一批早期的自然資源和環(huán)境保護法規(guī)。但盡管如此,資源銳減和環(huán)境惡化長時間并未真正成為人們普遍關注的熱點問題,直到20世紀,具有廣泛民眾基礎的自然資源和環(huán)境保護運動才得以頻繁涌現(xiàn)。在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的代表——美國,第一次大規(guī)模的自然資源和環(huán)境保護運動出現(xiàn)在西奧多·羅斯福執(zhí)政期間(1901—1909年)。作為美國歷史上“第一個懂得建設性地對企業(yè)文明所產生的問題作出反應的總統(tǒng)”,羅斯福極力主張通過國家干預保護自然資源和生態(tài)環(huán)境。在美國人民的大力支持和呼應下,羅斯福政府最終通過并推行了包括把重要自然資源收歸國有,組建由政治家、科學家和企業(yè)家共同參與的全國自然資源保護委員會,建立自然保護區(qū)和森林防護制度等在內的若干重大資源和環(huán)境保護措施。如果說美國第一次自然資源和環(huán)境保護運動主要是由當權者自上而下策動的因之其民眾基礎尚欠明顯的話,那么,發(fā)生于20世紀60--70年代的新環(huán)境保護主義運動(New Conservation Movement)則純粹是民眾反對集中而不負責任的公司權力的一次自覺行動。1970年4月22日,即第一個地球日那一天,這場運動被推向高潮,有1500所大學、1萬多所中學、1000萬多中小學生以及大量環(huán)保主義者、工商界開明人士和政府官員參加示威游行,抗議大企業(yè)忽視環(huán)境保護的行徑。新環(huán)境保護主義運動的影響是巨大的,以至于“到1973年,實質性的變化出現(xiàn)了,環(huán)境問題首次成為比公民權利更為重要的新聞。”此外,在這場運動中,各種各樣民間或半民間的環(huán)保組織紛紛出現(xiàn)或得到發(fā)展,它們包括山巒俱樂部(Sierra Club)、納德搜查隊、環(huán)境保護基金會(Environmental Fund)、全國自然資源保護委員會(National Resources Council)、荒野協(xié)會(Wilderness Society)、奧杜邦協(xié)會(Adubon Society)、全國野生動物聯(lián)合會(National Wildlife Federation),等等,這些組織對日后美國自然資源和環(huán)境保護運動的持續(xù)開展以及相應立法步伐的加快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第三,以倡導消費者主權、維護消費者權利為宗旨的消費者運動波瀾壯闊,成為20世紀各國經濟、社會生活中的一道耀眼的景觀。美國是消費者運動的發(fā)源地,早在1891年,就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個旨在保護消費者權益的消費者組織——紐約消費者協(xié)會,1898年,各州消費者組織又聯(lián)合組成了世界上第一個全國性的消費者組織——美國消費者聯(lián)盟(Consumer Federation Of America)。消費者組織的成立,點燃了消費者運動的星星之火。20世紀上葉,在消費者組織的領導下,消費者首先在與其關系最大、問題最多的食品和藥品領域掀起了一場場以爭取潔凈食品和藥品為目標的斗爭。進入60年代以后,通過拉爾夫·納德(Ralph Nader)等美國現(xiàn)代消費主義的奠基人的不斷努力,消費者運動涉及的領域進一步拓展,開始從食物和藥品等一般消費品逐步延伸到汽車等耐用消費品,并進而觸及公私機構對消費者受損事件的受理態(tài)度、服務質量、環(huán)境損害、消費者自我保護意識的培養(yǎng)、壟斷定價等眾多方面。消費者運動的蓬勃開展,也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視,1962年,肯尼迪總統(tǒng)提出了消費者的四大權利,即安全權、了解權、選擇權和意見受尊重權;1969年,尼克松總統(tǒng)又提出了消費者的第五項權利,即索賠權。在當局的支持和干預下,近幾十年來,美國各種民間的和官方的消費者維權組織如雨后春筍,茁壯成長;消費者權益保護立法也日臻豐富和完善。此外,在世界上其他國家,大規(guī)模的消費者運動雖然比美國出現(xiàn)得晚,但其發(fā)展勢頭亦十分猛烈。如德國于1953年成立消費者同盟;英國和日本分別于1957年和1966年成立消費者協(xié)會,各國成立的其他全國性和地方性的民間消費者組織更是難計其數(shù)。這些消費者組織既是消費者運動蓬勃開展的產物,同時又推動著消費者運動向縱深方向的發(fā)展和消費者保護立法的進程。
第四,尤其引人注目的是,20世紀以來,盡管理論界對企業(yè)社會責任正當性的爭論從未停息過,但在企業(yè)實務界,企業(yè)應在利潤目標之外承擔社會責任的主張得到了日益廣泛的認同;企業(yè)通過社會責任行動,致力于社會問題之解決,也逐步成為一種較為普遍的現(xiàn)象。在企業(yè)社會責任理論之爭最為激烈的美國,20世紀以來,許多知名大型企業(yè)的管理者都在企業(yè)的年度報告或其他場合明確表示支持企業(yè)社會責任。例如,科羅拉多燃料與鋼鐵公司曾公開宣布,企業(yè)目的,就是“解決社會問題”;美國鋼鐵公司和國際收割機公司董事伯金斯(George W. Perkins)早在1908年即提出:“公司愈是大型化,則它對全社會的責任就愈重”;著名企業(yè)家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也認為:隨著時代的發(fā)展,公司不能再一味地抱守私人利益,以使某些個人得以積聚財富而不顧那些參與財富形成過程的人的福利、健康與快樂,相反,我們應當接受現(xiàn)代的觀點,將產業(yè)作為社會服務的一種形式,惟利是圖只會引起對抗和招致麻煩。在這些開明企業(yè)家的領導下,美國的許多企業(yè)都通過不同的方式,投身于社會改良運動。僅就公司慈善捐贈而言,20世紀即獲得了長足發(fā)展。在理論界對企業(yè)社會責任持保守態(tài)度的英國,近年來也有相當多的企業(yè)界人士接受了企業(yè)社會責任思想,并通過他們的努力付諸了實踐。一位英國學者于1989年進行的一項關于企業(yè)社會責任的問卷調查顯示,在提供有效反饋信息的163家開放式公司和48家封閉式公司中,75%的開放式公司和71%的封閉式公司都將社會責任列為其主要目標;94%的開放式公司和90%的封閉式公司都對慈善或其他類似機構提供過捐贈;至少有86%的開放式公司和90%的封閉式公司都從事過慈善捐贈以外的他種贊助活動;許多公司都通過團隊簡報、雇員年度大會、雇員報告等形式為雇員參與公司事務提供方便,只不過此等雇員參與離真正意義上的產業(yè)民主和員工分享決策權尚有很大差距。此外,為了促使企業(yè)致力于公益事業(yè)的發(fā)展,英國企業(yè)界還發(fā)起成立了相應的自律性組織,如百分數(shù)俱樂部(Per Cent Club)、社區(qū)企業(yè)聯(lián)盟(Business in the Community)、志愿者中心(the Volunteer Centre)、慈善援助基金會(Charities Aid Foundation)、英國藝術援助協(xié)會(the Association for British Sponsorship of the Art)等。這些團體形成于企業(yè)社會責任運動中,同時又對企業(yè)社會責任運動的進一步開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最后,頗為明顯的是,20世紀前期的企業(yè)社會責任運動大都是各國國內呈現(xiàn)的現(xiàn)象,且主要致力于本國一些具體矛盾的解決,但在20世紀中后期,隨著企業(yè)引發(fā)的社會問題日漸突出,尤其是全球貧富懸殊的進一步拉大,以及跨國公司對世界影響力的與日俱增,企業(yè)社會責任運動也逐步發(fā)展成為一股勢不可擋的國際潮流;它所關注的問題也更具廣泛性和全局性,除傳統(tǒng)的勞動者和消費者權益保障、生態(tài)環(huán)境和自然資源保護等項目外,諸如維護人權、消除貧窮、遏止腐敗、創(chuàng)造社會公平、縮小工業(yè)化國家與發(fā)展中國家之間勞工標準和工資待遇上的差異等宏大目標的實現(xiàn),都被認為與塑造企業(yè)的適當角色緊密相關。在世界知名社會活動家和國際組織的推動下,企業(yè)社會責任運動的國際合作日益增強。近年來,在企業(yè)社會責任運動國際舞臺上,最引人注目的是利昂·H·沙利文教士及其主張。
沙利文是從關注南非的反對種族隔離斗爭開始而逐漸成為美國著名人權領導人的,他在1977年發(fā)表的“南非原則”提出了南非種族隔離期間在那里投資的標準,幫助許多公司下決心從南非撤出了投資,對實現(xiàn)社會變革施加了壓力。在發(fā)達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的一些跨國大公司高級代表的合作下,沙利文還主持起草了一套旨在指導在全球經濟發(fā)展中的公司行為的新規(guī)則,即“沙利文全球原則”,這些原則包括了沙利文所倡導的“對社會負責任的公司,無論大小,都可以作為目標來調整內部政策和慣例的參照標準。”該倡議于1999年11月由聯(lián)合國在紐約舉行的一次儀式上正式宣布,聯(lián)合國秘書長安南主持了這一儀式,有50多家世界大公司的代表出席,此舉表明國際社會已廣泛認同“沙利文全球原則”;按照要求,簽署這項原則的公司將密切關注本公司的業(yè)績,并就義務的實施情況發(fā)表年度報告。除“沙利文全球原則”外,聯(lián)合國還在1999年提出私營部門與聯(lián)合國之間簽署“全球協(xié)定”,其內容與“沙利文全球原則”大致相同,目的是吸引跨國公司支持全世界在維護人權、改善勞動條件和保護環(huán)境方面所做的努力。
該協(xié)定確定了9點“核心價值觀”,并且要求私營部門予以支持。這9點價值觀是從《人權宣言》、國際勞工組織(ILO)關于基本原則和權利的宣言、1995年哥本哈根社會問題最高級會議、1992年聯(lián)合國環(huán)境和發(fā)展大會的《里約環(huán)境與發(fā)展宣言》中摘選出來的,它們得到了世界經濟論壇、國際商會、國際勞工組織和聯(lián)合國的其他組織,以及幫助制定該協(xié)定的國際雇主組織的贊同,一些有名望的大公司也已公開表示支持這些標準。與此同時,各種企業(yè)社會責任論壇快速發(fā)展且活動頻繁,如著名的“企業(yè)——人道主義論壇”為使企業(yè)“成為許多人賴以生存的活動的資金保管者,支持以民眾為中心的價值觀”,就一直在大力倡導企業(yè)為欠發(fā)達國家和地區(qū)的人道主義活動承擔更多的責任。許多國際組織還在按企業(yè)社會責任的要求積極醞釀新的企業(yè)行為標準,如經濟合作與發(fā)展組織自1999年起即著手修訂“跨國公司準則”,以期建立一套對全社會負責的跨國公司行為基準。以上情況意味著,世界經濟的全球化正在使世界逐步發(fā)展成單一的經濟空間,企業(yè)作為這個空間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所扮演的角色和發(fā)揮的作用已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注意,人們期望它們在世界經濟和社會的健康發(fā)展中所承擔的責任也在日益增多。誠如聯(lián)合國秘書長安南在談及企業(yè)的社會作用時所言:伴隨著全球影響力而來的是全球責任。